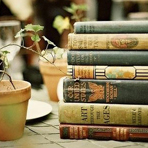‘中’者,别于外之辞也,别于偏之辞也,亦合宜之辞也”。什么意思
全部回答
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,表现在称谓上,除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外,又古今名号(如诸夏、华夏、中国、中华、禹迹、九州、赤县神州等)众多,域外称谓(如支那、赛裏斯、桃花石、契丹等)繁杂。
本篇讨论“中国”名号的来源与演变。按“中国”这一名号,历史久远,先秦时即已存在。然而,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,“中国”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;从夏、商、周直到大明、大清,都有自己的国号,并不称中国。
那麽,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什么含义呢?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跨古今、括全域的通称的?在文化上都有些什麽象徵意义?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?这些问题,都需要进行考证,予以梳理。1 一、释“中”释“国” 《说文解字》:“中,内也,从□│,下上通也。
”段《注》:“下上通者,谓中直或引而上,或引而下,皆入其内也。 ”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。据于省吾的考证,在殷商甲骨文及商、周金文中,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,向右或向左飘,“本象有旒之旗”;商王有事,立此以招集士众,士众围绕在此周围以听命,故而又引伸出中间之中的意思。
2由中间之中,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。 《说文》释中为内,又释内为入,段玉裁则发挥之:“中者,别於外之辞也,别於偏之辞也,亦合宜之辞也。”段说甚是。盖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没有两端,就不会有中间;没有四方,就不会有中央。中作为地理用语,乃对外而言,乃别偏而言。然则中的涵义,又不独仅此,在文化上,中显得更为可贵,“天地之道,帝王之治,圣贤之学,皆不外乎中”3,故古人视中尤重。
就为政而言,要“允执其中”4,“用其中於民”5;就立身而言,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”6,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,守常不变;就处世而言,中为“天下之大本”7;古人论道,也以中为归旨:“中即道也,道无不中,故以中形道。
”8以此,文化上的中,为正为顺,为和平,为忠信,为合宜。 中既具备了上述美义,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。文化名人夏丏尊〈误用的并存与折中〉9略说: 从小读过《中庸》的中国人,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与习惯。
凡遇正反对的东西,都把它并存起来,或折中起来。已经用白话文了,有的学校,同时还教着古文。已经改了阳历了,阴历还在那裏被人沿用。 已经国体共和了,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。讨价一千,还价五百。
再不成的时候,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。这不但买卖上如此,什麽“妥协”,什么“调停”,都是这折中的别名。中国真不愧为“中”国哩。 然则国字又作何解?《说文解字》:“国,邦也,从□,从或。”南唐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:“国,邦也,从□或声。
□其疆境也,或亦域字。”段《注》:“邦、国互训,……古或、国同用。”又《说文》:“或,邦也,从□从戈以守一。一,地也;域,或又从土。”段《注》:“或、国在周时为古今字。
古文只有或字,既乃复制国字,以凡人各有所守,皆得谓之或,……而封建日广,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,乃又加□而为国。 ……(或)从土,是为后起之俗字(即域)。” 按殷商甲骨文没有或、国二字。
周金文国字早期作或,以表示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;后期孳乳为国者,盖加□以为国界,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。 中与国两字连在一起,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--中国。 二、中国名号的起源 1963年,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,其铭文云:“唯王初迁宅于成周。
……武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曰:余其宅兹中或,自之乂民。”这段铭文的意思是:成王初迁居于成周(成周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)。先是武王克商后,在庙廷祭告于天说:我将居此中或,自此治理民政。
又《尚书·梓材》:“皇天既付中国民,越厥疆土于先王”,先王指武王。本诸上述,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,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;《梓材》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,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。
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,则中国名号已见于西周武王时期,当是可以肯定的。 更追溯之,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知道那时商人称他们的国为中商、商方;卜辞及典籍中,商王都所在又称大邑商。
10《说文解字》:“邑,国也,从□”;段《注》:“古国、邑通称。《白虎通》曰:夏曰夏邑,商曰商邑,周曰京师。 ……(□)音韦,封域也。”于省吾〈释中国〉也指出:“古文字的或、国、邑三个字的构形有着密切的联系,故《说文》既训或与国为邦,又训邑为国。
……甲骨文屡见‘大邑商’之称,商代乃‘城邦制’,故以‘大邑商’代表商国。” 商而称中商、商方者,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(如羌方、鬼方、苦方、人方等)而言。 方即国,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“维彼四国”,郑《笺》:“四国,四方也。
”方既是国,则中商、商方也可称作中商国。 商而称大邑商者,则是相对四土以及四方而言。甲骨文称:“东土受年,南土受年,吉。西土受年,吉。北土受年,吉。”这是说占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;此外,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屡见,四方指四方远处的方国。
而所谓四土、四方,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。 商既可称中商国,则去掉商字,正是中国,胡厚宣因说:“商而称中商者,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”11;田倩君也指出:邑既训国,则大邑商就是称谓中国之义,“准此‘中国’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。
”12 总之,中国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;商代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,却也形成了中商、商方、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,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名号始于商代,也不为过分。 三、地域概念的中国及其地域范围的扩大 中国一名自西周初期出现以来,迄于战国,依据当时及后来人的说法,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,也不尽一致。
其一,指京师。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:“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……惠此京师,以绥四国。”以中国和京师互称,正表明其涵义相同,以此西汉毛《传》解释道:“中国,京师也。 四方,诸夏也。
”又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:“夫然后之中国,践天子位焉”,南朝宋裴駰《集解》引东汉刘熙曰:“帝王所都为中,故曰中国。” 按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,它是中央之都城,是天子所居之城。如此,则中国指京师,盖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对四土的观念。
其二,指国中,国都。 《春秋榖梁传》昭公三十年:“中国不存公”,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,晋范宁《注》:“中国犹国中也。”按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,城圈以内为国中,城圈以外为郊,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;住在城圈裏的人称“国人”。
这一概念,西周时已然存在;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,所以到了春秋时期,当列国强大起来后,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,看待境内的属邑时,遂以中国自居。 如《国语·吴语》:“吴之边鄙远者,罢而未至,吴王将耻不战,必不须至之会也,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。
”吴韦昭注:“中国,国都。” 以中国指国中、国都,较之以中国指京师,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,即从为周天子专用,扩展到为诸侯共用,而所指称的范围则仍以城圈为限。 其三,指王畿。 《周礼·大司寇》:“凡害人者,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,以明刑耻之。
其能改过,反于中国。”郑玄《注》:“反于中国,谓舍之还于故乡裏也。”郑氏以中国为乡里,而乡里实等于近畿,属王畿以内之地。又《左传》昭公九年:“允姓之奸,居于瓜州。伯父(晋)惠公归自秦,而诱以来,使逼我诸姬,入我郊甸,则戎焉取之。
戎有中国,谁之咎也?”是周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。 周的郊甸既可称中国,则承此例,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,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,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。 其四,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。
《诗·大雅·荡》:“文王曰咨,咨女殷商。女炰烋于中国,敛怨以为德”;又说:“内奰于中国,覃及鬼方。 ”这是作者借周文王历数商王罪恶,使中国以至远方各族怨怒的告诫,来警刺周厉王。
又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:“天降丧乱,灭我立王。降此蟊贼,稼穑卒痒。哀恫中国,具赘卒荒。靡有旅力,以念穹苍。”诗中的中国也显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。惟春秋时,列国逐渐强大,形势有了变化,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。
其五,指诸夏国家。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--周国既可称中国,分封的诸侯列国--诸夏也不甘居后,况且诸夏国家的利害相对于四夷来说,与周大体一致,于是中国也可用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。
《左传》成公七年:“中国不振旅,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,无吊者也夫。”这裏的中国,与诸夏之义相当。 又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”,何晏《集解》:“诸夏,中国也。
” 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,遂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。上面已说过,列国初封时尚是一些城邦国家;以后,按照“诸侯立家”的原则,以扩建都邑的办法,又分封了许多贵族之家。
于是本来是距离遥远的许多城邦,逐渐扩大为境界相接并拥有大片领土的国家。不过各国间的疆界还不很固定,边界上的城邑时常成为争夺的对象;而随着国与国之间“隙地”(无人区)的越来越少,列国疆域终于连成一片,换言之,即一个一个的“中国”并为一体,如此,中国终于扩展为列国全境的称号。
其六,指地处中原之国。诸夏国家相对四夷都统称中国了,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,文化有高低,因此在习惯上,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,那些位置近(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)、文化高的诸夏国家,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周边的位置远、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。
然而,位置之远近、文化之高低并不是绝对的,以此,此义的“中国”所涵盖的国家也不会凝固。 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周世中国地”条尝论春秋之世,“其中国者,独晋、卫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许而已”,至于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,皆为蛮戎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,此本非中国的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,随着疆域的扩大或文化的进步,也逐渐得忝或一时得忝中国名号。在春秋先后成为霸主的诸侯中,就有秦穆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 霸主之国作为诸夏的重心,“尊王攘夷”的主角,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其进入中国的行列。
到战国后期,魏、赵、韩、齐、秦、楚、燕七雄,事实上就都被视为中国了。 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,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,它与上述的中国“指诸夏国家”含义近同;把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,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。
总括来看,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,积有六义。推此六义的演变,则开始发生的时间,大体一义比一义晚;所指称的对象与地域范围,也基本上后者比前者为多为广。然而比较而言,第五、第六两义发生的时间既晚,沿用的时间也较久,涵盖面则最大。
在此两义的中国的背后,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,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、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已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,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。
然而进一步推求,地域概念的中国,其名则一,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,再变而至於五、六变?且每一变基本上都是指称对象的增多而不是减少,指称地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?思之,当因中国文化上为一美名,中国代表著一种文化标准。
四、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的伟大 中字具有诸多美义,上文已述;而由中字之美义,又使中国成为一美名。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:“赵氏,中央之国也,杂民所居也,赵居邯郸,燕之南,齐之西,魏之北,韩之东,故曰中央。
”盖训中国为中央之国,其名已美;更求之,则中国之为美名者,尚不仅此。 《战国策·赵策》记公子成谏赵武灵王胡服,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: 臣闻之,中国者,聪明睿知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
今王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学者,离中国,臣愿大王图之。 是中国之为中国者,其人则聪明睿智,其用则万物所聚,其礼则至佳至美,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;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,即不得在中国之列。
文化概念的中国,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。也就是说,文化上达此标准者,即为中国;反之则为蛮夷。文化是不断进步的,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,而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。 文化的中国意义之伟大,正在于此! 文化的中国地域范围之不断的放大,又有个过程。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周世中国地”条: 成周之世,中国之地最狭。以今地理考之,吴、越、楚、蜀、闽皆为蛮,淮南为群舒,秦为戎,河北真定、中山之境乃鲜虞、肥、鼓国,河东之境有赤狄里(甲)氏、留吁、铎辰、潞国。
洛阳为王城,而有杨拒、泉臯蛮氏,陆浑、伊洛之戎。京东有莱、牟、介、莒,皆夷也。杞都雍丘,今汴之属邑,亦用夷礼。邾近于鲁,亦曰夷。 按洪氏所云,即大体以文化立说。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,春秋以至战国之世,大体已中国化;而老牌的中国如鲁、齐、晋、宋、蔡、陈诸国,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国化也并非一蹴而就。
如鲁号称旧邦,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云: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,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‘何迟也?’伯禽曰:‘变其俗,革其礼,丧三年然后除之,故迟。’”是鲁,周初分封时尚未完全中国化,其他可想而知。
西周以后,鲁、齐、晋、宋、陈、蔡、卫、曹等国,或以宗周之懿亲,或以前代之华阀,其为中国,已无疑义,而细揆其境内,蛮夷戎狄之非中国者,如洪迈所言,却也纵横参互于其间。 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戎狄或居于陆浑,东至于卫,侵盗暴虐中国,中国疾之”;又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:“平王之末,周遂陵迟,戎逼诸夏。
自陇山以东,及乎伊、洛,往往有戎。”“中国”内部尚且如此,“中国”以外的四夷就更多,更加交错复杂,如戎、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,夷分布在江淮至沿海地域,楚的南部则有群蛮和百濮。 上述“中国”内部的蛮夷戎狄及“中国”四周的蛮夷戎狄,自春秋时代起,迄于秦汉统一前,则大体已中国化者居多;而这一成果的达成,又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。
其一,民族同化。春秋时代,同化蛮夷彰彰可考者,如“齐之经营山戎,则山东、河北之境固。……晋之经营陆浑、姜戎、东山、骊戎,则山西之土定。 ……楚之经营百濮、南蛮、滇池,江汉之间、黔滇之域,举而入诸中国。
”13及战国时代,诸侯内竞,则赓续春秋以来遗绪,杂居于内地的蛮夷戎狄各部族,遂为诸夏国家所同化;诸侯外拓,则“东北有燕之拓土,东北、河北已固矣。北有赵之拓土,河北已定矣。南有楚之拓土,湖广滇黔已启矣。
西有秦之拓土,甘陇巴蜀已平矣。”14于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蛮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统一,被融合,或退处更远的边陲,于是在一个连成一体的相当大的范围内,都中国化了。及秦统一后,中国之范围更加恢廓。
其二,观念转变。唐韩愈《原道》: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
”是中国、蛮夷之分,不在族类,不在地域,而在文化;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又可以说:中国以文化成!中国者,文化之中国;若没有中国文化,在其后两千多年裏,又何以能混杂融汇数千百人种,而保持中国如故?而地域的中国渐趋扩大?而政治的中国愈益巩固?。
本篇讨论“中国”名号的来源与演变。按“中国”这一名号,历史久远,先秦时即已存在。然而,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,“中国”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;从夏、商、周直到大明、大清,都有自己的国号,并不称中国。
那麽,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什么含义呢?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跨古今、括全域的通称的?在文化上都有些什麽象徵意义?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?这些问题,都需要进行考证,予以梳理。1 一、释“中”释“国” 《说文解字》:“中,内也,从□│,下上通也。
”段《注》:“下上通者,谓中直或引而上,或引而下,皆入其内也。 ”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。据于省吾的考证,在殷商甲骨文及商、周金文中,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,向右或向左飘,“本象有旒之旗”;商王有事,立此以招集士众,士众围绕在此周围以听命,故而又引伸出中间之中的意思。
2由中间之中,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。 《说文》释中为内,又释内为入,段玉裁则发挥之:“中者,别於外之辞也,别於偏之辞也,亦合宜之辞也。”段说甚是。盖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没有两端,就不会有中间;没有四方,就不会有中央。中作为地理用语,乃对外而言,乃别偏而言。然则中的涵义,又不独仅此,在文化上,中显得更为可贵,“天地之道,帝王之治,圣贤之学,皆不外乎中”3,故古人视中尤重。
就为政而言,要“允执其中”4,“用其中於民”5;就立身而言,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”6,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,守常不变;就处世而言,中为“天下之大本”7;古人论道,也以中为归旨:“中即道也,道无不中,故以中形道。
”8以此,文化上的中,为正为顺,为和平,为忠信,为合宜。 中既具备了上述美义,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。文化名人夏丏尊〈误用的并存与折中〉9略说: 从小读过《中庸》的中国人,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与习惯。
凡遇正反对的东西,都把它并存起来,或折中起来。已经用白话文了,有的学校,同时还教着古文。已经改了阳历了,阴历还在那裏被人沿用。 已经国体共和了,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。讨价一千,还价五百。
再不成的时候,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。这不但买卖上如此,什麽“妥协”,什么“调停”,都是这折中的别名。中国真不愧为“中”国哩。 然则国字又作何解?《说文解字》:“国,邦也,从□,从或。”南唐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:“国,邦也,从□或声。
□其疆境也,或亦域字。”段《注》:“邦、国互训,……古或、国同用。”又《说文》:“或,邦也,从□从戈以守一。一,地也;域,或又从土。”段《注》:“或、国在周时为古今字。
古文只有或字,既乃复制国字,以凡人各有所守,皆得谓之或,……而封建日广,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,乃又加□而为国。 ……(或)从土,是为后起之俗字(即域)。” 按殷商甲骨文没有或、国二字。
周金文国字早期作或,以表示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;后期孳乳为国者,盖加□以为国界,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。 中与国两字连在一起,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--中国。 二、中国名号的起源 1963年,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,其铭文云:“唯王初迁宅于成周。
……武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曰:余其宅兹中或,自之乂民。”这段铭文的意思是:成王初迁居于成周(成周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)。先是武王克商后,在庙廷祭告于天说:我将居此中或,自此治理民政。
又《尚书·梓材》:“皇天既付中国民,越厥疆土于先王”,先王指武王。本诸上述,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,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;《梓材》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,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。
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,则中国名号已见于西周武王时期,当是可以肯定的。 更追溯之,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知道那时商人称他们的国为中商、商方;卜辞及典籍中,商王都所在又称大邑商。
10《说文解字》:“邑,国也,从□”;段《注》:“古国、邑通称。《白虎通》曰:夏曰夏邑,商曰商邑,周曰京师。 ……(□)音韦,封域也。”于省吾〈释中国〉也指出:“古文字的或、国、邑三个字的构形有着密切的联系,故《说文》既训或与国为邦,又训邑为国。
……甲骨文屡见‘大邑商’之称,商代乃‘城邦制’,故以‘大邑商’代表商国。” 商而称中商、商方者,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(如羌方、鬼方、苦方、人方等)而言。 方即国,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“维彼四国”,郑《笺》:“四国,四方也。
”方既是国,则中商、商方也可称作中商国。 商而称大邑商者,则是相对四土以及四方而言。甲骨文称:“东土受年,南土受年,吉。西土受年,吉。北土受年,吉。”这是说占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;此外,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屡见,四方指四方远处的方国。
而所谓四土、四方,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。 商既可称中商国,则去掉商字,正是中国,胡厚宣因说:“商而称中商者,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”11;田倩君也指出:邑既训国,则大邑商就是称谓中国之义,“准此‘中国’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。
”12 总之,中国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;商代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,却也形成了中商、商方、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,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名号始于商代,也不为过分。 三、地域概念的中国及其地域范围的扩大 中国一名自西周初期出现以来,迄于战国,依据当时及后来人的说法,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,也不尽一致。
其一,指京师。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:“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……惠此京师,以绥四国。”以中国和京师互称,正表明其涵义相同,以此西汉毛《传》解释道:“中国,京师也。 四方,诸夏也。
”又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:“夫然后之中国,践天子位焉”,南朝宋裴駰《集解》引东汉刘熙曰:“帝王所都为中,故曰中国。” 按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,它是中央之都城,是天子所居之城。如此,则中国指京师,盖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对四土的观念。
其二,指国中,国都。 《春秋榖梁传》昭公三十年:“中国不存公”,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,晋范宁《注》:“中国犹国中也。”按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,城圈以内为国中,城圈以外为郊,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;住在城圈裏的人称“国人”。
这一概念,西周时已然存在;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,所以到了春秋时期,当列国强大起来后,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,看待境内的属邑时,遂以中国自居。 如《国语·吴语》:“吴之边鄙远者,罢而未至,吴王将耻不战,必不须至之会也,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。
”吴韦昭注:“中国,国都。” 以中国指国中、国都,较之以中国指京师,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,即从为周天子专用,扩展到为诸侯共用,而所指称的范围则仍以城圈为限。 其三,指王畿。 《周礼·大司寇》:“凡害人者,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,以明刑耻之。
其能改过,反于中国。”郑玄《注》:“反于中国,谓舍之还于故乡裏也。”郑氏以中国为乡里,而乡里实等于近畿,属王畿以内之地。又《左传》昭公九年:“允姓之奸,居于瓜州。伯父(晋)惠公归自秦,而诱以来,使逼我诸姬,入我郊甸,则戎焉取之。
戎有中国,谁之咎也?”是周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。 周的郊甸既可称中国,则承此例,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,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,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。 其四,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。
《诗·大雅·荡》:“文王曰咨,咨女殷商。女炰烋于中国,敛怨以为德”;又说:“内奰于中国,覃及鬼方。 ”这是作者借周文王历数商王罪恶,使中国以至远方各族怨怒的告诫,来警刺周厉王。
又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:“天降丧乱,灭我立王。降此蟊贼,稼穑卒痒。哀恫中国,具赘卒荒。靡有旅力,以念穹苍。”诗中的中国也显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。惟春秋时,列国逐渐强大,形势有了变化,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。
其五,指诸夏国家。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--周国既可称中国,分封的诸侯列国--诸夏也不甘居后,况且诸夏国家的利害相对于四夷来说,与周大体一致,于是中国也可用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。
《左传》成公七年:“中国不振旅,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,无吊者也夫。”这裏的中国,与诸夏之义相当。 又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”,何晏《集解》:“诸夏,中国也。
” 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,遂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。上面已说过,列国初封时尚是一些城邦国家;以后,按照“诸侯立家”的原则,以扩建都邑的办法,又分封了许多贵族之家。
于是本来是距离遥远的许多城邦,逐渐扩大为境界相接并拥有大片领土的国家。不过各国间的疆界还不很固定,边界上的城邑时常成为争夺的对象;而随着国与国之间“隙地”(无人区)的越来越少,列国疆域终于连成一片,换言之,即一个一个的“中国”并为一体,如此,中国终于扩展为列国全境的称号。
其六,指地处中原之国。诸夏国家相对四夷都统称中国了,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,文化有高低,因此在习惯上,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,那些位置近(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)、文化高的诸夏国家,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周边的位置远、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。
然而,位置之远近、文化之高低并不是绝对的,以此,此义的“中国”所涵盖的国家也不会凝固。 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周世中国地”条尝论春秋之世,“其中国者,独晋、卫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许而已”,至于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,皆为蛮戎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,此本非中国的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,随着疆域的扩大或文化的进步,也逐渐得忝或一时得忝中国名号。在春秋先后成为霸主的诸侯中,就有秦穆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 霸主之国作为诸夏的重心,“尊王攘夷”的主角,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其进入中国的行列。
到战国后期,魏、赵、韩、齐、秦、楚、燕七雄,事实上就都被视为中国了。 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,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,它与上述的中国“指诸夏国家”含义近同;把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,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。
总括来看,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,积有六义。推此六义的演变,则开始发生的时间,大体一义比一义晚;所指称的对象与地域范围,也基本上后者比前者为多为广。然而比较而言,第五、第六两义发生的时间既晚,沿用的时间也较久,涵盖面则最大。
在此两义的中国的背后,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,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、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已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,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。
然而进一步推求,地域概念的中国,其名则一,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,再变而至於五、六变?且每一变基本上都是指称对象的增多而不是减少,指称地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?思之,当因中国文化上为一美名,中国代表著一种文化标准。
四、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的伟大 中字具有诸多美义,上文已述;而由中字之美义,又使中国成为一美名。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:“赵氏,中央之国也,杂民所居也,赵居邯郸,燕之南,齐之西,魏之北,韩之东,故曰中央。
”盖训中国为中央之国,其名已美;更求之,则中国之为美名者,尚不仅此。 《战国策·赵策》记公子成谏赵武灵王胡服,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: 臣闻之,中国者,聪明睿知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
今王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学者,离中国,臣愿大王图之。 是中国之为中国者,其人则聪明睿智,其用则万物所聚,其礼则至佳至美,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;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,即不得在中国之列。
文化概念的中国,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。也就是说,文化上达此标准者,即为中国;反之则为蛮夷。文化是不断进步的,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,而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。 文化的中国意义之伟大,正在于此! 文化的中国地域范围之不断的放大,又有个过程。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周世中国地”条: 成周之世,中国之地最狭。以今地理考之,吴、越、楚、蜀、闽皆为蛮,淮南为群舒,秦为戎,河北真定、中山之境乃鲜虞、肥、鼓国,河东之境有赤狄里(甲)氏、留吁、铎辰、潞国。
洛阳为王城,而有杨拒、泉臯蛮氏,陆浑、伊洛之戎。京东有莱、牟、介、莒,皆夷也。杞都雍丘,今汴之属邑,亦用夷礼。邾近于鲁,亦曰夷。 按洪氏所云,即大体以文化立说。吴、越、楚、秦、燕等国,春秋以至战国之世,大体已中国化;而老牌的中国如鲁、齐、晋、宋、蔡、陈诸国,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国化也并非一蹴而就。
如鲁号称旧邦,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云: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,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‘何迟也?’伯禽曰:‘变其俗,革其礼,丧三年然后除之,故迟。’”是鲁,周初分封时尚未完全中国化,其他可想而知。
西周以后,鲁、齐、晋、宋、陈、蔡、卫、曹等国,或以宗周之懿亲,或以前代之华阀,其为中国,已无疑义,而细揆其境内,蛮夷戎狄之非中国者,如洪迈所言,却也纵横参互于其间。 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戎狄或居于陆浑,东至于卫,侵盗暴虐中国,中国疾之”;又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:“平王之末,周遂陵迟,戎逼诸夏。
自陇山以东,及乎伊、洛,往往有戎。”“中国”内部尚且如此,“中国”以外的四夷就更多,更加交错复杂,如戎、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,夷分布在江淮至沿海地域,楚的南部则有群蛮和百濮。 上述“中国”内部的蛮夷戎狄及“中国”四周的蛮夷戎狄,自春秋时代起,迄于秦汉统一前,则大体已中国化者居多;而这一成果的达成,又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。
其一,民族同化。春秋时代,同化蛮夷彰彰可考者,如“齐之经营山戎,则山东、河北之境固。……晋之经营陆浑、姜戎、东山、骊戎,则山西之土定。 ……楚之经营百濮、南蛮、滇池,江汉之间、黔滇之域,举而入诸中国。
”13及战国时代,诸侯内竞,则赓续春秋以来遗绪,杂居于内地的蛮夷戎狄各部族,遂为诸夏国家所同化;诸侯外拓,则“东北有燕之拓土,东北、河北已固矣。北有赵之拓土,河北已定矣。南有楚之拓土,湖广滇黔已启矣。
西有秦之拓土,甘陇巴蜀已平矣。”14于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蛮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统一,被融合,或退处更远的边陲,于是在一个连成一体的相当大的范围内,都中国化了。及秦统一后,中国之范围更加恢廓。
其二,观念转变。唐韩愈《原道》: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
”是中国、蛮夷之分,不在族类,不在地域,而在文化;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又可以说:中国以文化成!中国者,文化之中国;若没有中国文化,在其后两千多年裏,又何以能混杂融汇数千百人种,而保持中国如故?而地域的中国渐趋扩大?而政治的中国愈益巩固?。
热点推荐
热度TOP
相关推荐
加载中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