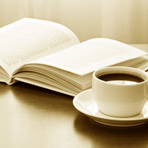中国最早提出“德政”的国家领导人是谁?
全部回答
皋陶是中国“德政”思想的人,生活于约公元前23世纪到前22世纪之间,东夷族部落首领,历经尧、舜、禹三个时代,在部落联盟中担任“士师”一职。相传他架构了中国最早的法律体系,被尊为“中国司法鼻祖”;他强调“法治”与“德政”的结合,形成“皋陶文化”,为后世儒家文化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精神渊薮之一。
后世人将皋陶与尧、舜、禹齐名,一同奉为“上古四圣”。 春秋战国时期,能形成一个诞生理想主义的宽松环境,在于东周父权家长制在最高层次的崩溃,和分封导致全局混乱,让各诸侯无暇巩固本国的统治秩序,而让位于支援对外战争,使得天下人有所喘息。
这本身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但是,农业经济的基础本身无法改变,以及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禁锢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,加之在以往的漫长年代所根深蒂固的父权核心思想,使得父权家长制在中国依然占据主流,只是统治形式有所调整。
春秋战国时期,诸子百家的思考,都无法超出这种先天的束缚。最终,占据了历史主流的思想,仍旧是拥护父权的儒家,只是,又从人伦纲常等各种角度稳固了这种“天理”,还加入了“仁政”等润滑剂,使之显得更人性化,更容易推行,让梦想“平天下”的知识分子有了更确切的理论依赖。
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朝代里,父权统治者们,正式将周朝式的“单纯的父权家长统治”,发展到“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”,分封制这种幼稚的方式被基本抛弃了,而进入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时代。 无论从官僚机构的设置上,还是对人民的思想教化上,都不择手段地限制人性的越级,将人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秩序的一个环节当中,为绝对的父权统治服务。
从此以后,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性灵光一现的中国人,在后两千年“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”的不断加强直至登峰造极的过程中,成为了“依附人”、“奴性人”,而实质上,都是私欲和内斗发达,而人性和灵魂却站立不起来的“成年孩童”。
孔丘基于他对周礼时代的解读和向往,和理想的君子式人格,开创了其儒家学说,以其儒家理论,组合起一个君臣父子,各安其等级,守其本分的等级制社会。他对这种道德支撑的结构,以及其统治者,存有强烈的幻想。
根据后世门徒的整理,孔丘的学说,主要分为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三个部分。 仁,解作“二人”,其实就是“人”,因为“人”需要在二人对应的关系中才能存在,单个的人只能叫做“身”,被看作是空虚而不存在精神之自我的。
“仁”也是被孔丘理想化后的人。它包括孝、悌、忠、恕、礼、知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内容,这些无一不是“二人”的人伦关系结构中的相对交际原则,而并不存在立于个人角度的客观原则。 基于周礼中所规定的等级制度的框架,位于各个层次的人,都应该具备的“二人”的伦理道德--仁,以在上下平行间和谐人际,达到安守本分的目的。
比如,子民对君主忠心,君主爱民保民。人与人之间,宽厚,恭顺,等等。孔丘把“二人”之中的“人性”设定得过于单纯美好,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安于自身的处境,而拿道德当饭吃,一想到天下有秩序了,精神就无比知足而蔑视物质。
这种“人”,更倾向于孔丘基于道德崇拜的感情加工产物,实则脱离了真正的人。人生而是独立的个体,以“我”为本位,有个体欲望,有追求个体独立自由的本能。孔丘以道德为本位,不知不觉抹杀了人,把人化为道德符号后,成为安定自足的附庸,这让后世的父权统治者利用起来,实在是太方便了。
礼,是“仁”的外在表现。孔丘说,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区区六个字,几乎是几千年中国人的一大精神写照。中国人是怎么“立”起来的?中国人没有以“仁”为内涵的“礼”,他就无法站立,无法行动,无法与人打交道,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明人。
孔丘首先把超出人性的“仁”转化为真实的人,又把“仁”的外在表现“礼”内化为人的一部分。 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,躯干四肢可以自由活动,这本身就能立了。但是当人被扭曲为“仁”之后,就必须以“礼”来成为新的四肢,代替我们本来的躯体的行动。
可见,这种扭捏作态的“礼”,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异化。人的本来的部分被掩盖,而增加了新的部分。这并不是孔丘的专利,我们不能怪孔丘,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 这种异化的人,丧失了人的本来,却升格出一种飘渺的审美,就像中国的人物画一样。
在后世,根本就做不到“仁”的中国人,也要说“仁”,也会讲礼,也要摆正面孔。这些,便渐渐形成了中国式脱离实质的形式主义。而中国人却始终无法从本真的人性中去发掘真理。 古人说,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。
孔丘的出现实属一种必然。在我们这样一个温驯而感性的农耕民族当中,每一个时代都诞生着无数的道德崇拜者。孔丘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,是基于中国人的道德崇拜、祖先崇拜,而对父权家长制的一种反思、诠释和肯定。
儒家思想,也绝不是孔丘这个人出现后的偶然产物,而是时代的催生,其在乱世以后大行于世也是必然。 因为它承袭了道德崇拜,完整了等级社会中的道德,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等级制度和人治的合理性,所顺应的,正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根本潮流。
然而,不论孔丘在后世被套上了何种非人性的光环,和何种利用。孔丘的人格、孔丘的仁爱精神,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十分令人感动。我们可以去阅读《论语》,来认识孔丘。 这本书既非道貌岸然的说教,也不是名言警句的堆砌,后世道学家的误读大大歪曲了《论语》当中那个活生生的真挚淡泊的孔丘。
孔丘受到了至圣先师的崇拜,却丧失了人的面孔。多少人说过他崇拜孔丘,但真正的爱孔丘,是源于受了一种简朴人性的触动,是在阅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一次次的人性共鸣。 孔丘自始至终都从人出发,对人更是一种简单真诚的爱,对理想的人格也充满了美好的寄托。
若以人的眼光来看待孔丘,以人的角度来还原孔丘,才能发现,所谓的“圣人”与自己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。
后世人将皋陶与尧、舜、禹齐名,一同奉为“上古四圣”。 春秋战国时期,能形成一个诞生理想主义的宽松环境,在于东周父权家长制在最高层次的崩溃,和分封导致全局混乱,让各诸侯无暇巩固本国的统治秩序,而让位于支援对外战争,使得天下人有所喘息。
这本身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但是,农业经济的基础本身无法改变,以及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禁锢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,加之在以往的漫长年代所根深蒂固的父权核心思想,使得父权家长制在中国依然占据主流,只是统治形式有所调整。
春秋战国时期,诸子百家的思考,都无法超出这种先天的束缚。最终,占据了历史主流的思想,仍旧是拥护父权的儒家,只是,又从人伦纲常等各种角度稳固了这种“天理”,还加入了“仁政”等润滑剂,使之显得更人性化,更容易推行,让梦想“平天下”的知识分子有了更确切的理论依赖。
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朝代里,父权统治者们,正式将周朝式的“单纯的父权家长统治”,发展到“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”,分封制这种幼稚的方式被基本抛弃了,而进入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时代。 无论从官僚机构的设置上,还是对人民的思想教化上,都不择手段地限制人性的越级,将人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秩序的一个环节当中,为绝对的父权统治服务。
从此以后,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性灵光一现的中国人,在后两千年“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”的不断加强直至登峰造极的过程中,成为了“依附人”、“奴性人”,而实质上,都是私欲和内斗发达,而人性和灵魂却站立不起来的“成年孩童”。
孔丘基于他对周礼时代的解读和向往,和理想的君子式人格,开创了其儒家学说,以其儒家理论,组合起一个君臣父子,各安其等级,守其本分的等级制社会。他对这种道德支撑的结构,以及其统治者,存有强烈的幻想。
根据后世门徒的整理,孔丘的学说,主要分为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中庸”三个部分。 仁,解作“二人”,其实就是“人”,因为“人”需要在二人对应的关系中才能存在,单个的人只能叫做“身”,被看作是空虚而不存在精神之自我的。
“仁”也是被孔丘理想化后的人。它包括孝、悌、忠、恕、礼、知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内容,这些无一不是“二人”的人伦关系结构中的相对交际原则,而并不存在立于个人角度的客观原则。 基于周礼中所规定的等级制度的框架,位于各个层次的人,都应该具备的“二人”的伦理道德--仁,以在上下平行间和谐人际,达到安守本分的目的。
比如,子民对君主忠心,君主爱民保民。人与人之间,宽厚,恭顺,等等。孔丘把“二人”之中的“人性”设定得过于单纯美好,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安于自身的处境,而拿道德当饭吃,一想到天下有秩序了,精神就无比知足而蔑视物质。
这种“人”,更倾向于孔丘基于道德崇拜的感情加工产物,实则脱离了真正的人。人生而是独立的个体,以“我”为本位,有个体欲望,有追求个体独立自由的本能。孔丘以道德为本位,不知不觉抹杀了人,把人化为道德符号后,成为安定自足的附庸,这让后世的父权统治者利用起来,实在是太方便了。
礼,是“仁”的外在表现。孔丘说,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区区六个字,几乎是几千年中国人的一大精神写照。中国人是怎么“立”起来的?中国人没有以“仁”为内涵的“礼”,他就无法站立,无法行动,无法与人打交道,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明人。
孔丘首先把超出人性的“仁”转化为真实的人,又把“仁”的外在表现“礼”内化为人的一部分。 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,躯干四肢可以自由活动,这本身就能立了。但是当人被扭曲为“仁”之后,就必须以“礼”来成为新的四肢,代替我们本来的躯体的行动。
可见,这种扭捏作态的“礼”,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异化。人的本来的部分被掩盖,而增加了新的部分。这并不是孔丘的专利,我们不能怪孔丘,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 这种异化的人,丧失了人的本来,却升格出一种飘渺的审美,就像中国的人物画一样。
在后世,根本就做不到“仁”的中国人,也要说“仁”,也会讲礼,也要摆正面孔。这些,便渐渐形成了中国式脱离实质的形式主义。而中国人却始终无法从本真的人性中去发掘真理。 古人说,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。
孔丘的出现实属一种必然。在我们这样一个温驯而感性的农耕民族当中,每一个时代都诞生着无数的道德崇拜者。孔丘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,是基于中国人的道德崇拜、祖先崇拜,而对父权家长制的一种反思、诠释和肯定。
儒家思想,也绝不是孔丘这个人出现后的偶然产物,而是时代的催生,其在乱世以后大行于世也是必然。 因为它承袭了道德崇拜,完整了等级社会中的道德,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等级制度和人治的合理性,所顺应的,正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根本潮流。
然而,不论孔丘在后世被套上了何种非人性的光环,和何种利用。孔丘的人格、孔丘的仁爱精神,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十分令人感动。我们可以去阅读《论语》,来认识孔丘。 这本书既非道貌岸然的说教,也不是名言警句的堆砌,后世道学家的误读大大歪曲了《论语》当中那个活生生的真挚淡泊的孔丘。
孔丘受到了至圣先师的崇拜,却丧失了人的面孔。多少人说过他崇拜孔丘,但真正的爱孔丘,是源于受了一种简朴人性的触动,是在阅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一次次的人性共鸣。 孔丘自始至终都从人出发,对人更是一种简单真诚的爱,对理想的人格也充满了美好的寄托。
若以人的眼光来看待孔丘,以人的角度来还原孔丘,才能发现,所谓的“圣人”与自己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。
热点推荐
热度TOP
相关推荐
加载中...